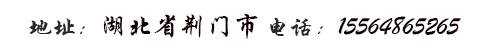李世民真的那么爱哭吗
|
来源:知乎 作者:秋菊落英 这么有意思的问题我一定要来回答一波! 这么说吧,可以负责任地告诉题主:论起中国历代帝王中最能哭的人,李世民若认了第二,绝对没人敢认第一!刘皇叔简直冤枉死了好吗…… 前面 玛莉蓓尔已经把李世民为妻子儿女哭的事迹说了很多了,我就主要说说功臣好了:不夸张地讲,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几乎每一位都与李世民有一段眼泪的故事。唐朝人自己都对太宗皇帝的这种性格了如指掌,白居易那首著名的《七德舞》中就有一句:“魏徵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你看这对仗对得多好啊!先看魏征的上联: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重,李世民亲临其家探望;后来李世民梦到魏征与自己告别,醒来后就听人奏报说魏征去世了,于是感叹道:“从前商王武丁在梦中得到了良臣傅说,朕却在睡醒之后失去了贤臣。”(“魏征疾亟,太宗梦与征别,既寤,流涕,是夕征卒。故御亲制碑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今朕失贤臣于觉后。”——《白氏长庆集》自注)。 这是白居易写的,而李世民自己呢,也写了两首送别魏征的诗: 一首《望送魏征葬》: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一首《魏徵葬日登凌烟阁》: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馀形无复人。(《魏郑公谏录》卷五) ——看到了吗?全都没离开眼泪! 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旧唐书·魏征传》再来看张公谨的下联: 张公谨曾在玄武门之变时独自“掩门拒敌”,又在担任代州都督期间上书《言突厥可取之状》六条,是李世民最为倚重的功臣之一。贞观六年四月,张公谨去世,年仅39岁。李世民为其发丧那天是辰日,古人都很迷信,认为辰日哭泣是忌讳,但李世民却说:“感情发自内心,怎么能因为日子而有所避讳呢?”依旧为张公谨恸哭了一场。 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旧唐书·张公谨传》至于其他人,只要翻翻史书,就会发现李世民为功臣而哭泣的故事真的是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年轻的小秦王时期就开始了: 武德五年,太原元老殷开山病逝于征讨刘黑闼的路上——“复从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 武德七年,“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病重,李世民将其接入府中,与其相拥话别——“寻命舆疾诣府,太宗亲以衣袂抚收,论叙生平,潸然流涕。寻卒,年三十三。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直到即位后,李世民还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又因为梦到薛收生平,赐其家粟帛。 这两次,李世民分别只有23岁和25岁。 李世民还有一位“小迷弟”李道玄,从15岁起跟随秦王东征西讨,十分崇拜身先士卒的二哥,每次都要先登陷阵,经常被射的像刺猬一样。后来二征刘黑闼,李世民被调回,李道玄因副将史万宝救援不及而阵亡,年仅19岁。李世民为此悲伤了很久,贞观初年忆起此事仍忍不住流涕。 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终始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惜其年少,不遂远图。"因为之流涕。——《旧唐书·列传第十·宗室》之所以把李道玄的故事放在后面讲,是因为贞观二十二年底又发生了一件事: 曾经抚御高昌、大破焉耆、更早之前还在洛阳城下献策“一战擒二王”的安西都护郭孝恪,在攻破龟兹都城后,因失于警备,导致流亡在外的龟兹国相又设计夺回了都城。郭孝恪仓促应战,中流矢而死。重病中的李世民听到战报,责备郭孝恪轻敌,但后来又悯其战死,为其举哀。 城中举应那利,孝恪殊死斗,中流矢卒,子待诏亦殁。将军曹继叔进兵,复拔其城。太宗责孝恪斥候不明,至颠覆,夺其官。后愍死战,更为举哀。——《新唐书·郭孝恪传》看了这两个故事,就会明白我国的文字记载在世界文明传播史上那BUG般地位绝对不是白给的:李世民追忆李道玄的时候,一开始还是“从容谓侍臣曰”,结果说完就哭了;对郭孝恪也一样,一上来先责备其战败丧师,但没过多久悲悯就盖过了愤怒——这让我想起了东野圭吾笔下那些“即便办过再多的凶杀案,也无法习惯悲伤”的刑警,对于李世民来说,就是“经历过再多的出生入死,都无法从容面对身边人的离去”吧,从25岁到52岁都是如此。 再来看看著名的类书《册府元龟》为我们做的总结吧(感叹一下这种分门别类整理好的史书真是太好用了!)—— 在《帝王部·念良臣》篇中,提到了李世民在杜如晦、张公谨、虞世南、魏征、薛万均、李大亮、岑文本、温彦博、姜确等九位大臣去世后的表现,每一位都是甚哀、怆然、哭之甚恸。 太宗贞观四年,尚书右仆射杜如晦薨。帝手诏著作郎虞世南曰:“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奄从物化,追念勋旧,痛惜于怀。卿体吾此意,为制碑文也。”後因食瓜而美,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置之灵座焉。後赐房玄龄黄银带,因谓玄龄曰:“如晦与公同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因泫然下泣。以黄银辟恶,恐为鬼神所畏,令取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其後帝梦见如晦若平生,及旦以告玄龄,言毕唏嘘,侍卫莫不掩涕。光是一个杜如晦,李世民就至少哭了三次:吃到美味的瓜想起了杜如晦,怆然悼之,剩下半个瓜不吃了送去杜如晦灵前;赐房玄龄黄银带,只见房谋不见杜断,泫然下泣;后来又梦见了杜如晦,醒来跟房玄龄诉说,言毕唏嘘,把侍卫都给带哭了。 十二年,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卒……未几,作诗一篇,追思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锺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将何所视?”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而焚之。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后数岁,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旧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这里补充了一段《旧唐书》的内容:李世民不仅“哭之甚恸”,还感叹“锺子期死,伯牙破琴”,赋诗一篇发现无人应和又烧掉。后来梦见了虞世南,还为其造了天尊像一区(虞是南朝人,信佛),下敕绘虞世南像于凌烟阁。 (ps,写到这突然发现李世民不仅爱哭,还爱做梦,数过这是第几次了吗……) 是岁,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雒阳苑,甚恸。十九年,车驾征辽,中书令岑文本卒。帝亲临视,抚之流涕。其夕,帝闻岩鼓之声曰:“文本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遂命停之。姜确为左屯卫将军,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督兵攻盖牟城,中流矢而卒,时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为五言诗曰:“凿门初奉卫,仗节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未展六骑术,先亏一篑功。防身不足智,徇命有馀忠。悲骖嘶向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以上是李世民为李大亮、岑文本、姜确(姜行本)落泪的情景,就不逐一而表了。 而同一卷书中这段高士廉去世后的故事,算是李世民最为悲痛的时刻之一,有点长我不知道该如何节选,都贴这吧—— 二十一年,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薨。帝闻之流恸,将往哭之。房玄龄顿首谏曰:“陛下久御药石,不可临丧。去岁圣躬不安,康复甫尔,臣等敢以死请。”帝曰:“朕此行也,岂独君臣之礼欤?兼以故旧情深,恩戚义重,一朝长逝,忍而不哭之乎?卿等勿复言也!”乃从数百骑出兴安门,司徒长孙无忌哭於丧侧,闻驾来,驰往奉见,涕泣马前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臣之目见,诚有所徵。陛下含育黎元,须为宗社珍爱,臣亡舅士廉知将不救,尝谓臣曰:‘至尊覆载恩隆,不遗簪履,亡没之後,或致亲临。生存虚荷荣班,无酬圣德,安可以北首、夷衾,辄回銮驾?魂而有灵,负谴斯及。不愿亲临,期於必遂。’”其言甚切。帝终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涕泣交流。帝感之,还入宫苑,南望而哭,雨泗沾衣,从官无不屑涕。——《册府元龟?帝王部?念良臣》简单翻译一下:高士廉去世后,李世民将要亲往临丧,房玄龄苦劝无果。当时长孙无忌正在高家哭於丧侧,听说皇帝来了,拦在马前对李世民说,舅舅临终之前特地嘱咐“不要因为我的死而惊扰圣驾”,因为当时李世民久病初愈,临丧乃是大忌,但李世民还是不听。长孙无忌干脆躺在路中央涕泣交流,李世民这才肯离开,回宫之后登上城楼,南望而哭,泪如雨下,又一次成功把身边人全给带哭了。 其实并不非得是功臣去世,有时李世民怀念起过去的事情也是会哭的——比如有人告尉迟敬德谋反,李世民问他是否确有此事。尉迟敬德直接把衣服一脱,露出身上的一道道伤疤,李世民顿时就哭了,好言好语安慰了尉迟一番: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资治通鉴·唐纪十一》看到吧,尉迟敬德真可谓粗中有细,非常了解他这位老上级的脾气秉性,知道怎样能戳中李世民心里最软的地方——对比一下唐高宗时期,已经失势的褚遂良从桂州进一步被贬往爱州,临行前上表苦求,言及“先帝去世时,陛下手抱臣颈”的往事,企图打动李治,李治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类似地,上面高士廉那段也有体现:高士廉临终前对长孙无忌说“亡没之後,或致亲临”,认为李世民极有可能会不顾身体前来吊丧,可见贞观天子这种念旧的作风已经深入人心了。 或许,李世民的这种“铁血长情”的性格亦感染了他身边的大臣:贞观七年,著名的法官戴胄去世,不仅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与戴胄生前交好的房玄龄魏征也十分感怀,经过曾经同游的地方,亦忍不住哭泣。 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旧唐书·戴胄传》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深情的房玄龄在临终之前见到李世民会怎样呢?当然是一起哭啊!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微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之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资治通鉴·唐纪十五》最后,虽然说了这篇回答主要讲功臣,但结尾还是来讲讲李世民和子女之间的故事吧:不得不说,一生英武果敢的李世民在晚辈面前,时常会有一些打脸真香的表现啊…… 当初,既是太原功臣又是玄武门功臣的长孙顺德因为女儿去世伤心得一病不起,李世民是这样对房玄龄吐槽的:此人毫无阳刚之气,因为一点儿女之爱就得了大病,至于吗? 丧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胡足恤?"未几,卒,遣使吊之,赠荆州都督,谥曰襄。——《新唐书·长孙顺德传》然而贞观十七年,由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亲自抚养的掌上明珠晋阳公主因病去世,年仅12岁。李世民哀伤得一个多月没能好好吃饭,整个人瘦弱不堪。群臣都劝他节哀,李世民却说:“朕岂不知道悲伤无益?然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自已。” 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再次回顾一下前面高士廉去世那一段,李世民分别给其子高履行长孙无忌写了两张小纸条,对高履行说:“古人立孝,毁不灭身,闻卿绝粒,殊乖大体,宜抑摧裂之情,割伤生之累”,对长孙无忌说:“卿有风疾,宜须抑情。朕观履行,何可堪处?”——告诉高履行守孝要有度,绝食是不对的;告诉长孙无忌有慢性病“风疾”就要学会控制情绪,像高履行那样是不对的。 可是他自己呢?前一年才刚因为征高丽返回途中的痈疽、夏季的气疾、冬天前往灵州招抚薛延陀“冒寒疲顿”,一连大病了三场,结果刚过正月就要去高士廉家哭丧。房玄龄长孙无忌两大宰辅苦苦相劝“服药期间情绪激动是不对的”,却依然拒谏不听,你不让我临丧我回宫哭去! 房玄龄长孙无忌:白忙活了…… 还有《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第二》中,征高句丽临行之前教育李治的片段: 十九年,帝征辽,留皇太子在定州。将发,皇太子对帝悲啼者已数日。帝谓曰:“承乾凶悖,尔非次而得立。自为嫡长,常在吾膝前,与婴儿孺子奚异哉!而官寮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东征,故留尔作镇,亦冀天下之人见汝风彩……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岁偏孤,蒙陛下手加鞠养,自朝及夕,未尝违离。明旦辞违,陨心泣血。今日顿锺於臣,因悲不自支。”帝亦为之洒泪。具体就不啰嗦了,总之就是李世民临行前看到李治整天哭泣,觉得这孩子长不大,需要加强教育,结果李治一句“臣七岁丧母,是您亲手养大的”,反过来把李世民给弄哭了。 题主提到《贞观之治》,马跃在拍完这部剧接受采访时曾说:“最后我很难把马跃与李世民剥离开来。史书记载李世民爱哭,我很难统计我哭了多少回。每一次都是从心里流出来。可以说,我是欢乐着李世民的欢乐,悲伤着他的悲伤。”——其实《贞观之治》的剧本主要采自《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已经比纪传体的两《唐书》和类书《册府元龟》简略很多了。比如上面教育李治这段,通鉴就只保留了前半部分,删掉了李世民自己忍不住也哭了的后半部分(==)。还有很多其他功臣的传记,李孝恭啊李靖啊段志玄啊,我都准备好了但出于篇幅考虑都没有写。 总之,对比历史上的李世民,司马光对马跃真的算是“手下留情”了啊! 结尾发一张别人总结的图吧,侵删,个人觉得还挺应景的—— 哭了这么多,来补一个温馨的故事吧: 贞观时期著名的蕃将契苾何力,原为铁勒酋长的王子。贞观六年,契苾何力率众内附,被李世民授予左领军将军,随后又参加了唐灭吐谷浑、灭高昌的战争。 贞观十六年,契苾何力回到凉州省亲。当时正值薛延陀毗伽可汗势力强盛,铁勒诸部便带着契苾何力的母亲和弟弟投奔了薛延陀,并将契苾何力也绑了送到毗伽可汗的牙帐下。然而契苾何力宁死不屈,抽出佩刀对着东方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说完割下左耳,以示不可夺志。 与此同时,唐朝这边看到契苾何力迟迟不归,也有人对李世民说:“人心皆恋故土,契苾何力入了薛延陀,怕是如鱼得水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李世民却不以为然,对这些人说:“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 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就这样,双方互不知情却不约而同地坚守着对对方的忠诚与信任。后来终于有使者从薛延陀来到了唐朝,详细讲述了契苾何力身陷虏庭忠贞不渝的经过——然后,不出所料地,天可汗又被感动哭了: 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宗泣谓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旧唐书?契苾何力传》会使至言状,帝泣下。即诏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许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还。——《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李世民答应了许婚换回契苾何力,何力回朝后却力谏不可,提出要让薛延陀亲至凉州迎亲以表诚意——最后王子要回来了,公主也没嫁过去。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最终的结局: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在白岩城之战中,契苾何力率领精骑八百力挫敌军万余,冲突其阵、束疮而战,大破高丽军,追奔数十里,斩首千馀级; 总章元年,契苾何力与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一起,踏过鸭绿水,攻克平壤城,擒获了高丽王高藏、莫离支泉男建,献俘于昭陵。 ——这就是《贞观政要》所说的“君臣合契”的典范吧?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qiea.com/dqefbfw/9829.html
- 上一篇文章: 推荐书单原耽万人迷受合集part2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