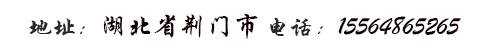自然在可亲近处七
|
↑牵牛花的一对开裂的蒴果,子室里是灰黑的小种子。 十二月 午后三点,穿上羽绒服,踏上棉靴,带上小相机,打算出西门沿人工运河走一圈儿,去看看冬芽和宿留果实。刚出单元门,西天的薄阳被河边那两幢高楼挡着,光线灰暗,穿行在绿地间那条小路,一小片丁香丛里传来暄闹的鸣叫。是成群麻雀落在枝梢上,有数十只之多,我一走近,它们突然集体噤了声,也没有飞走,只其中的一两只“啾”地叫上一声。不过半分钟的样子,它们又开始“叽叽喳喳”地啁鸣起来,兴高采烈地,操着我听不懂的鸟语,声音大到几近刺耳。俯身在草窠残雪间抠了一粒还没冻实成的石子下来,向林梢轻轻一抛——呼啦啦几十只麻雀纷纷跃起、展翅,一个小小盘旋,投奔不足半米远的另一丛枝梢去了。 ↑今年结的香椿子。 脚下棉靴踏着冬雪,走进小区里那片果木、灌木相杂的小树林。高阔的核桃树早抖落了全部叶子,光滑的青灰枝干裸露着,枝梢上的冬芽很小,看不真切。秋末时爬满虫子的那棵桑树,树干上仍附着不少生着银白色长毛的虫,一动不动,不知死活。与其相距不远的香椿树,树下有新落的几枝香椿子;今年五月末时,曾见其在枝冠生了许多长长的圆锥花序,原打算持续观察开花、结果,琐事繁杂,还是错过了。一棵西府海棠,托着细长果梗的小果子挂满枝梢,一棵山里红,一枝枝黄绿,绯红的冻果子,树下薄雪盖不住一地落果,这一个、那一个的小圆雪窝。去找长廊西南角的那几棵榛树,这几棵榛树种了三四年,近似一人多高的小灌木,观察冬芽更容易些;灰褐色、布满细刺的枝条上,鲜紫红色的潜伏芽,苞鳞覆瓦状,尚分辨不出哪个是叶芽,哪个是花芽。更惹眼的是深红色紧实的雄花短穗,互动或对生,像冬眠的虫蛹,冻得硬梆梆地挂在枝头。整个冬天,雄花序都不脱落的植物,倒是第一次遇见。 ↑榛树鲜紫红色的芽苞 ↑榛树正在“冬眠”的雄花序 在我透过相机镜头端详榛树雄花穗时,听到黄昏微光下灌木丛间传来一阵鸟鸣,出挑而清亮,放下相机,寻声瞭望,起初以为是蹲在楼宇顶层边缘的那两只大鸟,极目辨识了一会,那是两只鸽子。叫声又起,吡吡吱吱,全是上扬的摩擦音,又像两只吹得快要爆炸的气球相摩擦发出的声音。搜索不到鸟的踪迹,索性举着相机,镜头对着暗蓝天光里那一片木林梢影,录下那别致的叫声——突噜噜地一道黑鸟剪影自林梢弹出,双翅一张一翕,划一道波浪线,从我头顶掠过,先是在一棵枣树上停了下,又飞跃上一楼住户封闭阳台的平顶上,一跳一跳的,小脑袋左右张望着,开始新一轮聒噪鸣叫!它的叫声太出挑了,一只像好几只,热闹的很。抓拍到一张模糊的照片,发给同学辩认,原来是栗耳短脚鹎。 陪父母去看展览,一起去吃火锅,透过餐馆的玻璃窗,看到了天边很好看的云,只属于寒冷的冬天才有的云。如巨大的羽翼伸展,平沙漠漠间烟灰色的远山黛影,水天一色,微波漫卷的地平线。 上午十点,在檐前日暖的阳台又听到了栗耳短脚鹎的叫声(窗子仰开),往窗外一扫,看见两只栗耳在窗外的那棵毛白杨上落了下,又扑楞楞飞远了。忙不迭地换上保暖内衣,抓绒衫、羽绒服,套上厚秋裤、牛仔裤,长筒翻毛皮靴,背上单反相机冲出门去。(冬天出门真是又耗时又繁琐,鸟儿怕是早飞没影了。) 小区内的灌木丛躲在高楼的阴影里,从容走过互怼聊闲天的麻雀群,看过三五只结集打尖儿的灰喜鹊,没见到其它鸟种。落光了叶子的连翘差点没认出来,初夏长满叶子时也曾一脸茫然地在站在那儿认了好一会,最后是关于早春时那片金黄花海的方位感记忆帮了忙。这时节好认些,它那灰黄的枝条,特别是枝条上的梭形潜伏芽,竟和早春时见到的花苞一模一样。花期过后的整个炎夏、暖秋,它都在繁茂的叶子掩护下,悄悄地孕育、生长,为明年早春开花做着准备;当寒风摇落黄叶,粒粒冬芽才露出端倪,神似腊嘴雀结实的短喙。难怪它春日花开早,那不是春风化雨带来的奇迹,而是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准备,等着被三月末突如其来的一波回暖天气激活,迅速萌发、开花、传粉…… ↑连翘的休眠花苞 一棵海棠树,几个椭圆的“洋辣”壳嵌在小枝枝桠处,壳质坚硬,描着银白、灰棕相杂的长条纹,有的完好,有的已经虫去壳空。我们俗称的洋辣子,其实是褐边绿刺蛾的幼虫,属鳞翅目刺蛾科,分布地域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它的幼虫表面的细毛如针,碰触后会让人痒痛难忍,因此俗称“痒辣子”,谐音“洋辣子”。洋辣壳则是刺蛾幼虫越冬时在树枝上做的石灰质的茧室。小时候在乡下,冬日里男孩们常常在杨榆槐树间寻摸洋辣壳,不为好玩,是为了吃。胆大的把抠下来的洋辣壳放牙齿间,轻轻一咬,一只鹅黄色肉虫子就现身了;胆小的用小锤子敲,力道要刚刚好,不然壳里的肉虫就被砸扁了,然后用细棍挑着蠕动的虫子近火烤熟,趁热吃掉! ↑西府海棠小枝上的“洋辣壳”。 小区西门不远,一株细高小灌木,小枝稠密处挂着一只马蜂蜂巢,像一只干枯的大莲蓬。蜂巢直径约10cm,单层垂直排列的纸质巢室约百个,开口向下,有些室口还封着一层米色薄茧,里面多半封着没能成功羽化的蜂蛹。在《冬日的世界》里海因里希感叹:“用了大约3亿年来完善它们建筑技术的昆虫的巢穴或许是地球上最早期的巢之一,迄今仍是最精妙的建筑之一。”那么,在城市里最有机会能够欣赏到的精妙建筑,就是马蜂的圆盘状蜂巢了。 马蜂筑巢不像蜜蜂那样使用自己分泌的蜂蜡,而是先将草或树的纤维咀嚼并与唾液混合后,再用其构筑出纸样的巢。立冬时节,母亲曾用棍子捣掉了卧室窗檐上的一只马蜂窝,我如获至宝,将它做为大自然的艺术品收藏。这只巢颜色银灰,亚光纸质感,长约5cm,宽4cm,深3cm,巢上方较平坦,泡沫纹,没有孔洞,只偏离中心有一小丘状突起,用以将整个巢固定在窗檐的水泥造面上。巢室约有40个,向下开口六边形,孔口大开,里面全部都是空的。我用小镊子挨个孔室探寻了一遍,只在一个孔室里夹出一点蛹壳残片。我试着用手剥开最外边的一个孔室,室壁米白,只在近基部染上一抹焦棕色,也许是蜂后为了固定卵和幼虫,制造了更为坚韧的丝状物留下的痕迹?做了随时屏住呼吸,迎接异样气味的心理准备,我把洞开的巢室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居然是淡淡草木香! 我问母亲这个蜂巢存在多久了,今年有马蜂住在里面吗,她说两年了,今年一直空着,没见马蜂进出,所以才敢大大方方地捅掉。我又问每年开春,马蜂会像燕子住回自己的旧窝吗?一般不会,但常常会有马蜂在旧窝附近建新窝,所以要把空窝赶紧启走。我记起母亲曾说起过,以前在乡下时,她摘豆角时被马蜂蜇了小手指,立刻肿得比大拇指还粗,疼得打不了弯。 ↑拍这张照片时,我无法确定,挂着蜂巢的这棵树是什么树,这回方位记忆也没帮上忙,在日记里提醒自己明年春天来寻找答案。(今年五月末特意去看,远香来袭,油绿小叶间开着一穗穗小小的白色花串,原来是一棵辽东水腊。) (PS:今天,坐在电脑前整理照片、记录下这些文字时,才发现照片中马蜂巢下方的枝干上裹满白色发泡状物质,其间还有一枚棕红色茧壳。上网搜索,原是白蜡虫在幼虫时期分泌的蜡质,在辽宁地区,其多寄生在4~5年生以上的水蜡苗木上——哎呀妈呀!半年前的这张小照片上早已留下线索,可惜粗心大意的我并没有成功解读,最后只用了最笨的方法,等了长长的五个月才揭晓谜底。) ↑零上的暖水与零下的冷空气相遇,河上雾霭濛濛。 西门外的空地,宿雪未消,苔藓还绿。静静的人工运河沐浴在冬日阳光下,水气蒸腾,波光粼粼,一人立在桥栏边,看不清神情,偶尔呵气成烟,转瞬消失在寒风里。吸附在岸边防护堤石上的石螺,较深秋时少得多,零星几只趴在浅岸河泥上,不知是死是活。落光了叶子的山皂角树,枝干黢黑,树瘤虬结处生长的棘刺显得格外醒目,长如锥,短如针,幼刺坚实,是具光泽的棕红色,老刺稍扁,颜色棕紫,多分枝呈鹿角状刺团,最长的刺约有10cm。棘刺其实是特化的枝,无从知晓漫长的时空变迁里,山皂角是为了适应何种特别的生态环境而将枝条特化形成了这些尖刺。 ↑山皂角棘刺 山桃树枝上的冬芽苞已经长好,枝梢上挂着一两个风干的桃果,有的只宿存着一粒大桃核。有人将圆柏分泌的明棕色油脂收集在树干上部的一小截断梗上,如今冻得硬梆梆的,透亮如珀。在一棵长得很高的元宝槭(我借由枝梢宿留的翅果认出了它)上,发现一只鸟巢。巢材多为小树枝,巢沿边有几缕白丝棉和塑料布随风轻摇。是谁的巢呢?是留鸟的常驻巢还是夏候鸟的弃巢?站在小广场上那两棵老杨下仰头望了许久,一队又一队灰喜鹊在蓝天与树影枝格间翩然穿越而来,那情景美不可信,恍如仙乡幻境。 ↑元宝槭上的鸟巢 ↑圆柏分泌的明棕色油脂,透亮如珀。 就在快离开河岸边的这一小片灌木丛林间,栗耳短脚鹎那别致的鸣叫突然响起,好运气来得太突然,还是一对!端起相机追随着它们,从柳树到山皂角,又到金银木,其中的一只停了下来。镜头里,小家伙身体圆滚滚的,腹部羽毛蓬松,缩着脖子在吞食一颗金银木的小浆果,因枝影的遮挡,看不到栗色耳羽,只看见它亮晶晶的小圆眼睛和微微翘起的灰色冠羽。因鸟鸣而开始的一场冬日漫步完美收官,如此丰富又意外,遇见,探寻、发现,自然带来的,永远无法预知。 ↑栗耳短脚鹎 ↑栗耳短脚鹎 去体院打球一小时,带着小望远镜刚迈出球馆就听见了栗耳鹎的叫声从不远的小树林传来,不再喧闹、激越,哔-哔-唧-唧-,相应和着,温和叙说。更神奇的是自星期二偶然在自家小区听到它的叫声,狗仔队一样追随着它的身影从这棵树到那棵树再回到这一棵,躲在树下仰望,蹲在灌木丛间极目搜索,站在河岸透过望远镜看上个把小时,回来上网查询,刷照片刷视频听鸣叫,再认真写个自然笔记,画个儿童简笔画之后,就突然发现大冷的天竟哪哪儿都能遇见它们,看来已是数量稳定的冬候鸟了。 栖息在体院小树林的这一小群,有七八只,是本周第三次遇见。终于可以气定神闲地跟随着它们在树间转悠,透过望远镜看它们在圆柏致密的绿色鳞叶间啄食柏果,看它们一对一对落在松枝间隙一边晒着太阳梳理羽毛一边温和回应着同伴的鸣叫,看他们三三俩俩落在林边的水塘栈道,小脑袋一点,再扬起,咂着深黑的长喙饮冰水。这情形让人想起之前在豆瓣看到的话题,分享你的hygge时刻,那么这一刻便是了——当然请忽略冻得不太听使唤的双手和已被冷风攻陷、隐隐作痛的膝盖。 ↑冬阳下的运河 运河边走走停停,运河水光灼灼,水草冷绿,缓缓流过河沙乱石。一只小肥啾(麻雀)跟寒冬里遇到的大多数鸟类一样,蹲在向阳处,裹着厚厚的毛外套,衬着好像时刻准备要缩进毛大衣里的小脑袋瓜,像穿了卡通人物服装道具的小人儿。更多的麻雀躲在圆柏针叶层叠的枝干深处,鸣叫、晒太阳,整理羽毛,把头歪进羽翼里打盹儿。剪了几根山皂荚的棘刺,几棵刺槐树经年生在高楼的阴影里,树下拣到的几个种荚里,少有饱满的种粒。折了一枝金银木,枝上零星的正在风干的小红果子,掂起脚尖掳了一把小叶朴的黑果子,像一粒粒小药丸,难怪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黑弹树”。臭椿树上挂着一团团“沉甸甸”的翅果种序,最低的一团,跳起来也够不到,“人肉梯”今天没带在身边,不甘心地转来转去,像只偷不到葡萄的狐狸,终于在树下寻得一根山皂荚的枯树枝,一只手用它去压低最可能得手的一根臭椿树小枝,另一只手抓住小枝梢,终于摘了到一小穗像数只眼睛挤在一处的小翅果。细花梗上,臭椿翅果长约4cm,三五枚相叠,直径只有8mm的浅棕色小种子包裹在梭形膜翅的中央,轻薄如纸的膜翅描着细条纹,在顶端扭转,可以随风顺水轻松地带着种子远行。 ↑为抵北地苦寒,留鸟和冬候鸟都换上又厚又蓬松的体羽,看上去胖乎乎的。 ↑栗耳鹎爱吃的小果子(金银木) ↑洋白蜡的翅果果序 ↑臭椿树上挂着一团团“沉甸甸”的圆锥种序 此时,还能在枝间采集到宿存种子的树木有梓树、洋白腊、火炬树、元宝槭、栾树、圆柏、油松,还有白桦。大学校园间的小路旁,省图西南角的长椅后,突然发现城市里的白桦树也不少,三五成林,深秋一树橙黄,长冬里白净的树干格外醒目;踏着吱嘎作响的厚雪凑过去,能看见细枝条上互生的尖尖的鳞芽,枝头上和冬芽挤在一起的是深红色雄花序,冻得硬邦邦的,两穗人字型,三穗个字型;腋生的种穗只剩下细瘦的果序轴,偶尔寻见一穗深褐色细塔状种序,轻轻一碰,薄薄的苞片和种子一层层窸窣飘落而下。(抗冻能力超强的白桦雄花序,让我想起月初在小区里那几棵榛子树尖上挂着的暗红花穗,回来一查榛树居然也是桦木科。) ↑冬天的白桦 白桦的果序是的圆柱形球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轻轻碰下,一层层飞鸟剪影状的球果苞片像下雪一样散落下来,随之飘散的是无数带着膜翅的,昆虫模样的小坚果。那个完全脱落干净的果序轴,豆瓣的一位友邻说像一柄轻巧的剑,对,就是权利的游戏里二丫的“缝衣针”,哈哈。桦树树干多净直,树皮灰白,皮孔是深棕色“一”字纹,撕下其中翻卷的一条,能剥下分层的内皮,一层米白,一层淡橙,又一层奶白……每一层都薄滑柔韧,随手在上面写个字、画个小画都不错。据说距今年至年的青铜时代,在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曾有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桦树皮文化圈”,在这里生活的不同民族的人,都会使用桦树皮制成的器物,小到盛食物的器皿,狩猎工具,大到房屋、船只,至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赫哲族还会制作和使用一些桦树皮制作的生活用具。 ↑右上:白桦的雄花序左、中:白桦的果序 ↑白桦的果苞片和带膜翅的小坚果 在草丛间采了一小捧旋复花的干燥种子,茶条槭很有秩序感的长枝上挂满一簇一簇茶色翅果,小膜翅光泽闪映,像开了一树细碎花朵。天气很冷,空气很鲜,天空很蓝,一会功夫手已经冻得不太听使唤。快步冲向大片阳光普照的空敞时,发现小路旁一株小树上挂了一串一串浅咖色的果穗,种子已经不见,只剩果实苞片似覆瓦排列,拍了照片,传到形色,居然告诉我是大名鼎鼎的鹅耳枥,采了几个果穗回来,灯笼一样很好看。将小雪、大雪节气以来,收集到的种子和自然物摆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发到朋友圈,朋友留言:太美了,治好了我的长冬抑郁症。我回:种子是植物在秋天留给自己的记忆收藏夹。 那么,我孜孜不倦地在收集的是什么呢?我心上的缺撼与惶恐终将被什么治愈?有生以来遇见的人,看过的风景,走过的童年,离开的故乡,晦暗时刻,开怀瞬间,沉默如秘的自然万物给过的慰藉,都化作回忆点点滴滴,一粒一粒,生活的种子。我把它们收藏在相册里,硬盘里,日记本里,书里,漆盒里,每日餐桌的菜肴里,梦里,心里。等我老得出不了门,找一个个喝完的牛奶盒,再把它们一粒粒种下去,放到阳光最好的窗台上,一天浇浇水,一天松松土,候着它们破土,发芽,长叶,窸窣作响。一棵棵难忘的树,一个个想念的人,一场场风花雪月的事,都在这刻穿越时空粉墨登场,正开的花朵变成了舞台点亮,五光十色,香气跳荡。 ↑自然收集物:山皂角棘刺、白皮松树皮,白蜡树种穗、臭椿种穗、刺槐种荚、小叶朴果实,香椿子,卫矛蒴果、金银木浆果、山皂角荚、牵牛花籽、圆柏球果、侧柏鳞果、杜松子球果、油松松果、南蛇藤蒴果、鹅耳枥果穗、紫叶小檗浆果、栾树蒴果、辽东水腊果实、榛树雄花、山里红、西府海棠、梣叶槭翅果、紫苏子、山核桃、雪松松塔、杨树冬芽,共计二十八种。 阴霾天,穿越大半个小区去门口取快递。听见丁香、榆叶梅、红瑞木杂植的灌木丛里传来磔~磔~鸟鸣,站在近处凝神扫视了好一会儿,终于发现繁枝碎叶间一只大斑啄木鸟的背影,嗯,原来是你。顺路揪了两个干燥的萝藦果,一串风箱果的聚伞果序,几枚果翅呈小小锐角,果壳上覆着细茸毛的槭科翅果,这在枝头风干已久的翅果,大都轻触一下即分裂两半,然每一半仍然像小陀螺一样旋转飘落,很有意思。回来拍照片时去掉了果翅的槭树种子是一端平一端带尖刺的球状小坚果,好奇敲开了坚硬外壳,里面绿豆大小的果仁,不难吃,一点杏仁似的微苦。 ↑自然收集物:某槭翅果、辣蓼铁线莲种子、东北珍珠梅种序、桦树果序及体眠雄花穗、风箱果果序、萝藦蓇葖果、蛇床种序。 ↑蛇床的聚伞种序 ↑去掉了果翅的槭树种子是一端平一端带尖刺的球状小坚果。 而那两只米黄色萝藦蓇葖果,大毛笔头形状,一根弯转的柔韧果梗,用了很大力气才揪下来;其中一只果壳已裂开,近果梗端,数量惊人的褐色、水滴形、扁平小种子拖着一束束长长的白色丝状绢毛,很有秩序感的排列,紧实又妥贴在挤压在一起。轻轻拉出最外面的一枚,成束的种毛一下子弹开,比起蒲公英的小“降落伞”,萝藦的种子看起来更神似一只张牙舞爪的多足小蜘蛛。中了贝恩德?海因里希的蛊惑,我打算数数萝藦的一只蓇葖果里藏着多少枚种子。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代价是此后一个星期,我们家的扫地僧都举着一枚又一枚毛乎乎的“小蜘蛛”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一个!你到底带了什么回家? ↑答案是:。 去体院打球一小时后,出球馆在校园里溜达。折了一把东北珍珠梅别致的干花穗,采了鸡树条的簇生的伞序红色果实,一团大花圆锥绣球的姜黄色干燥花序,几根梓树细长如豇豆的种荚,外种皮裂开,里面带着柔毛的四边形小种子已所剩无已,国槐大多数串珠似的荚角还都缀在高高的枝梢上,一只栗耳短脚鹎时不时地拍打着双翅悬停着,啄食那些干燥的灰绿种荚。低头在树下找,终于找到一嘟噜,种角三五个,肉质种荚没有想像中的干燥,依然可以徒手剥开,粘腻沙感酷似果脯,闻上去有淡淡甘香,让人想起本地的冬令美食:干豆角。难怪那只栗耳短脚鹎那么卖力气,美食诱惑任谁也无法抵抗。 ↑鸡树条荚蒾的伞序浆果 我又从背包里拎出小望远镜出去找鸟(现在只要出门就把修枝剪、束口袋和袖珍望远镜塞进背包)。小檗丛里发现几只远东山雀,它们要么警惕性太高,要么饥饿难当,在枝间穿梭跳跃着寻找食物,每次停下不超八秒,正在镜头里追踪——突然离我不过一米远的国槐树干上蹿上来一只肥鸟!眼睛移出镜筒细打量,灰蓝背羽,淡白肚皮贴树皮,黑色过眼纹,尖细的略微上翘的小嘴,原来是一只普通?。为抵北地的苦寒,留鸟和冬候鸟都换上又厚又蓬松的体羽,多数看上去都胖乎乎的,而这小家伙,挺着“发福”的肚皮,大头向下,翘着小喙和短尾巴,停在树干上一动不动地四下张望的样子太可爱了。它不但能向下攀行,还喜欢飞快地用小嘴探啄进皮缝里找食物。裸眼观察普通?的功夫,这片小树林里,伴着“jie-jie-jie-jie……”尖细叫声,飞来几只长尾巴小鸟,是以前没见过的新鸟种。忙架起望远镜,移动镜头,调动轮盘对焦——终于看清了:它们身形娇小圆润,黑尾巴倒挺长,几乎与头身等长,嘴峰短小,好像在哪里见过——对啊,是在花椰菜的《银喉长尾山雀一家》那篇图文里。 ↑远东山雀 ↑被我认作银喉长尾山雀的小鸟,经友人甄别,是北长尾山雀。 天气太冷了,冻手冻脚,只好先钻进车子暖和一会儿,喝口热茶。不远处一棵漆树,只剩下在树冠上几十个“小红火炬”尚未熄灭,突然想去树下碰碰运气,便下车踩着吱嘎作响的冻雪凑了过去,看看能不能拣一个回来。其实明知道漆树那顽强的圆稚种序,多半到明年早春三月还会屹立在枝头。“小火炬”自然没找到,一起身却发现漆树南边的一棵云杉树,向阳的一面沐浴着阳光,树桠、小枝及针叶上的碎雪薄冰正在消融,半树星光闪闪烁烁,霜绿的针叶间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两只袖珍小鸟若隐若现。有那么一眼看到它们黄黑色肩羽,以为是黄眉柳莺(可它们现在应该在南方猫冬呀),不敢再靠近,只好蹑手蹑脚地退出林地,跑回车子里取了8倍率的小望远镜,绕到那棵云杉的东南方向,透过镜头,以树干为轴,一层一层地在稠密的侧枝、小枝间搜寻,发现一只旋木雀,一边围着粗粝树干转着圈地向上攀行,一边用长而下曲的长喙翻检着翘起的树皮。 ↑旋木雀 就在我的镜筒追随着上扬时,枝桠上的一只小鸟突然闯进了圆形的视野框。 小巧的身体,头顶中央有一道前窄后宽的柠檬黄色冠羽,两侧各有一条黑色侧冠纹。黑亮的小圆眼睛,蓬松的黄绿褐色装束,看上去像个小毛球!哇噢!不会是小戴菊吧!我不敢相信也不敢确定。毕竟作为《冬日的世界》里第一主角,我刚在海因里希的文字里与之相遇并被它深深吸引,追随着它走进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天气冰冷、食物匮乏的冬天,惊叹于它展示出来的那些无法想像的神奇,甚至专门上网去找它的照片和视频,像个追星的小粉丝。在我被从天而降的好运砸得晕头转向的功夫,镜野里灰影一闪,又飞过来一只!它俩一边在小枝的尽头跳跃,旋转着啄食着什么,一边发出“zi-zi-zi-”的鸣音。“戴菊的嗓音很细,在人类的听觉范围里几乎听不见,除非你认真找它们,否则你即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存在。它们盘旋在树枝的尖端,在茂密的云杉树丛中不停地跳来跳去,啄食着几乎看不见的猎物。”乍一听,那声音细小到很容易被其它鸟鸣——旋木雀那一连串尖锐明亮的高音所淹没,甚至消失在风声或树声里。可一旦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看着它们在针叶与小分枝间不停地啄食,那少有停歇地鸣叫则清晰可辨,热情又欢悦。 戴菊即不喜欢吃雀类们在整个冬季都吃的植物种子。也够不到树皮底下或深埋在木头里的幼虫。它的小喙很适合从小树枝上搜索昆虫。但是在冬天有什么昆虫是可能四处活动的呢。海因里希用了四年时间知道了北美的金冠戴菊冬季的食物是变种飞蛾的幼虫,那么,在这儿猫冬的戴菊,在长达五个月的冬季在吃什么续命呢?它们格外青睐针叶树,云杉、圆柏,刺柏,这些树上冬季会用什么昆虫寄生越冬呢?它们会吃点云杉、圆柏的种子?还是某种蛾的幼虫?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能揭晓。而数年前那个在病人与诊室之间穿梭的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会因为遇见一只小小鸟而倍感幸福,还兴奋地挥着拳头对爱人说:今天是我的LuckyDay。 ↑云杉树影间,弹跳飞跃的戴菊 ↑正面像有点朋克:P 打扫房间,去机杨接儿子归家,一会大雪弥漫,一会雾雨纷纷。一场幕天席地的雨加雪之后是零下十几度的大晴天,人们化身帝企鹅在亮如镜面的小路上走得步步惊心。唯有走进一片针叶树冠覆盖的那一小段路,才长长吁一口气,步子迈得像个人类的样子。怪不得金冠戴菊选在雪杉枝下织巢呢,致密的针叶树影下,寻不见半点冰雪痕迹,硬梆梆的路面到了这里踏上去仍是厚重而松弛,一层灰铜色落叶也安静了许多,不禁嘴角上扬,记起盛夏曾在这躲避过一场急雨。 在校园里等人。池塘水流半冻,近堤岸处冻了厚厚的柳叶,林间数株树木枝干疏密丛生,蓬草衰落,群鸟雀跃,或飞或宿,或鸣或食。树下雪地光影交错,有人用树枝写大字“沈阳一日游”***题,明亮处有晶莹冰屑一闪又一闪。侧耳倾听,林间有细亮的鸟鸣,又远又近,也许是组队在杉柏树间觅食的戴菊、煤山雀,远东山雀。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在体院的小树林里拍到了远东山雀、旋木雀、栗耳鹎、北长尾山雀、还有小戴菊!零下十几度的正午观鸟、拍鸟一样不出半个小时就冻得瑟瑟发抖。虽然这个老单反相机拍出的效果不尽满意,仍然很开心。当然,较之拍鸟,还是像几天前那样拎个小望远镜伫立在树林雪地间,安静又贪婪地看着它们不停地跳跃、盘旋、啄食、发呆、拉屎、梳理羽毛,在树枝上磨蹭尖喙,感觉更美妙! 平安夜。用红松和油松松塔摆了个小圣诞桌,自制一棵小圣诞树,叶子都是夏秋时节压制的,做得很粗糙,好在有灯光加持,效果还不错。家人小聚甚欢,举杯愿来年一切遂平安。做了酱牛腱子,炸了茄盒、萝卜丸子,久在异乡的儿子居然最爱吃的是妈妈做的炝拌黄瓜干。 ↑炝拌黄瓜干 现在,那个我用文字、用镜头描摹的年,已经切割成为一小块一小块方方整整的时间,仿佛已久远到可以拿在手里细细端详,恍然如梦,又似袖底微风。彼时,与孩子洒脱地告别,怎知突然相隔大洋,不知归期何时?彼刻,怎知有一天数亿人囿于家中,一呼一吸都变得战战兢兢?生命的消逝,个体的悲喜,从来都不过是大漠一砾,苍海一粟,很多人都突然失去了现实与虚构的分辨力;巨大的幻灭感如一座悬崖,矗立眼前。好像能做的,只剩下清晨、午后或黄昏的长长漫步,搜寻一棵树、一朵花、一只鸟的微陌阡尘,带几片叶子、几块石头,落花、气味、鸟鸣、一些记忆和满脑子的问号回家。 “那些自然而然的不去破坏它,便是给你最好的礼物了。” Ps:年初春在VUE注册帐号,想做个“城里有四季,心中有自然。”的主题,最后一年将尽,不过是将手机里随手拍的素材七七八八叠在一起,还是老老实实写自然笔记吧。(想看的朋友可点文末阅读原文) 图:consuelo 文:康素爱萝 图文版权归东北*小栖之家所有 猜你喜欢: 自然在可亲近处自然在可亲近处(六)冬至:点鬓微霜,岁晏苍茫。盛京四季:家门口的草木日记的确,在沈阳,四季的美不那么显而易见,一开始真是要拿“放大镜”来看,但慢慢地你会意外之趣,树木,花朵,昆虫,燕雀,循着季节的韵脚,欣欣然相随而出,当土地,植物、天空的细微的变化你都能注意到,那可是非常惬意的时刻,试试看吧,哈哈!你会发现打量城市的角度有很多层面,平凡忙碌扰嚷的城市中,一样有草木飞鸟花朵昆虫,小小的自然毫不吝啬地呈现给世人美妙的胜景。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盛京城。写给乡园的一本小书沈复在《浮生六记》说:“布衣饭菜,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矣。这么微末的角度,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我知道有人在探店、尝遍地方小吃,在记录本地鸟类,昆虫,溯源穿城而过的河流,有人在走街穿巷寻访老建筑,老街牌,探访老民间技艺,录制口述历史或者收集地方俗语,民歌民谣等等。我多么希望,从个体出发,有越来越多关于地域文化、民间艺术,生活方式,传统民俗等方方面面的记录,这种来自民间的个体表达,会让我们的故乡家园或自己正在栖居的城市和村庄,在我们,我们的孩子心里变得具体,丰富、有意思。双12特惠当当、京东有售小栖之家:近处是新的远方。 点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qiea.com/dqewxtz/5953.html
- 上一篇文章: 研究中国发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
- 下一篇文章: 英文中的叠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