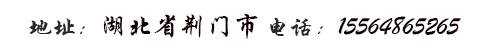付强霸姬盤銘文考釋
|
付强 上海三唐美術館 ------------------------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出土了一件氣盤(M∶5,其實這件盤,正確的命名,應該是霸姬盤,我們後文有論證。)。《考古學報》年第2期的發掘簡報對其進行了公佈。盤的形制,圓形,口微敞,窄折沿上翹,方唇。盤腹較深,上腹微鼓,下腹圓弧內收,圜底。下接大圈足,足壁斜直外張,底面平整。下腹附對稱雙耳,頂面與口近平。上腹飾顧龍紋一周,分四組,前後各二組,中部界以獸頭,每組三龍紋同向,兩組間龍首相對,兩側耳下腹壁龍尾相對。耳兩面飾鱗紋,圈足飾兩周凸弦紋。四分合范鑄成,雙耳與器體為一次鑄成。背面中部獸頭中間有一條豎向範線,耳內側腹部鳥紋間有二條豎向範線。打磨精細,未發現打磨痕跡。腹部墊片明顯。口沿、耳部及內外壁多處有縮孔。圈足內壁上部與內底交接處有六個三角形凸釘[1]。 氣盤 盤內底鑄銘文十行一百五十三字(含合文四、重文一) 下面按照我們的理解,結合簡報給出的釋文,把銘文寫出來: 1.唯八月戊申,霸姬以氣訟於穆公,曰:以公命用簋朕臣妾自氣,不余氣。 2.公曰:余不女命曰:霸姬。 3.氣誓曰:余某弗稱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鞭五百,罰五百寽。 4.報厥誓曰:余稱公命,用霸姬。襄余亦改朕辭,則鞭五百,罰五百寽。 5.氣則誓:曾厥誓曰:女某弗稱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則鞭身,傳出。 6.報厥誓曰:余既曰稱公命,襄余改朕辭,則出棄。 7.氣則誓。 8.對公命,用乍(作)寶盤盉,孫孫子子其萬年寶用。 我們把銘文分成了八小句,氣盤和之前公佈的氣盉屬於同一套器物,銘文也有關係,時代也相同,都屬於西周中期,我們把氣盉的銘文也寫出來。 氣盉銘文: 1.乞誓曰:余某弗爯公命,余自無,則鞭身,笰傳出。 2.報氒(厥)誓曰:余既曰,余爯公命,襄(曩)余亦改朕辭,出棄。 3.對公命,用乍(作)寶般(盤)盉,孫子子(其)邁(萬)年用。 下面對氣盤銘文進行逐句考釋: 1.唯八月戊申,霸姬以氣訟於穆公,曰:以公命用簋朕臣妾自氣,不余氣。 霸姬,當是霸伯的妻子。 訟,提起訴訟,屬於當時的法律訴訟術語,和匜銘文:“牧牛!乃可(苛)湛(勘)。女(汝)(敢)(以)乃師訟。”中的“訟”,意思一樣[2]。 穆公,西周中期的穆公見於以下金文中: 穆公鼎:穆公乍(作)旅。西周中期前段。 尹姞鬲:穆公乍(作)尹姞宗室于繇林,隹(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朢(忘)穆公聖粦明事先王,各(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君蔑尹姞,易(錫)玉五品,馬亖(四)匹,(拜)(稽)首,對(揚)天君休,用乍(作)寶。西周中期前段。 穆公簋蓋:隹(唯)王初女(如),廼自商(師)(復)還至於周,□夕,卿(饗)醴於大(太)室,穆公(侑)(禦),王兮(呼)宰□易(錫)穆公貝廿朋,穆公對王休,用乍作寶皇(簋)。 盠方尊:隹(唯)八月初吉,王各(格)于周廟,穆公右盠立於中廷,北卿(嚮)。西周中期前段[3]。 從以上的相關銘文看,穆公常常擔任周王冊命大臣時的佑者,所以穆公當是西周中期的王室大臣。 ,,釋為“僕”。,吳雪飛先生認為,從“馬”從兩“丙”,兩“丙”為“更(鞭)”字省體,像以鞭馭馬,為馭字。所以,這兩個字當釋為“僕馭”[4]。“僕馭”見於師毀銘文“僕馭、百工、牧臣妾”。 簋,字形作“”,此字是否是簋字,有學者表示懷疑。吴雪飞先生认为此字從“玄”(玄之古文,見于金文),疑讀為從行、玄聲之字,此字或作從行、言聲。《說文》訓為“行且賣也。”《廣雅釋詁三》訓為“賣也。以公命用玄朕僕馭臣妾自乞,即以公之命,從乞處賣給我僕馭臣妾,而乞不給我。不(余)予乞,可能是乞不(余)予的倒文。后来,吴先生又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將“用”后一字釋為從“玄”可能是錯的,當按照《發掘報告》釋為“簋”。懷疑此字可能讀為“鳩”,《爾雅釋詁》:鳩,聚也。《左傳》隱公八年:“以鳩其民。”注:“集也”《左傳》定公四年:“若鳩楚竟。”注:“鳩,安集也”。鳩朕僕馭臣妾,懷疑是安集我的僕馭臣妾的意思。此句含義有待進一步研究[5]。 這句話的大意是,八月戊申這天,霸姬把氣這個人向穆公提起了訴訟,說以穆公以前的命令,我的僕馭、臣妾,這些都要從氣他哪裡產生,換句話說,就是氣要給我提供我的僕馭、臣妾,但是現在氣他不給我。因為臣妾、奴僕,這種事發生爭執訴訟,還見於近年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出土的肅卣銘文[6],大家可以參看。 2.公曰:余不女命曰:霸姬。 這句話是穆公對氣說的,從“虎”,從“卜”,我們之前有小文章,考釋此字為“虐”[7],現在看是不對的。此字吳雪飛先生認為從虎從卜的字,當從卜聲,《爾雅釋詁》:卜,予也。《詩天保》:君曰:卜爾楚茨,卜爾百福。傳箋皆曰:予也。疑此字讀為卜,為給予的意思[8]。 我們同意他的看法。這句話的大意是,穆公對氣說的,我之前不是命令你給霸姬嗎,指的是之前穆公命令氣,要為霸姬提供僕馭、臣妾。 3.氣誓曰:余某弗稱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鞭五百,罰五百寽。 余某弗,見於盉銘,白軍鵬先生認為“某弗”為雙重否定,表示肯定[9]。西周中期後段的諫簋記王命,有“汝某不又有聞”,裘錫圭先生指出,楊樹達先生讀諫簋的“某不”為“無不”。他說:余按金文通以母為毋,本銘母敢不善引者按“母敢不善”緊接在“女某不又”下,即其例也。此某字亦當讀與母同。《說文?三篇上?言部》載謀字或作,又或作,此某與母音同之證。原注二字並咍部—引者按即之部—明母銘文於此句不言母而言某者,以下文已有母字,變文以避複也。又某聲古與無聲互通,《詩?小雅?小旻》:“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膴”作“腜”。《大雅?緜》:“周原膴膴”,“膴膴”《韓詩》作“腜腜”此其證也,女某否又昬,即女引者按讀“汝”無不有聞也[10]。 裘錫圭先生認為過去的金文研究者,多誤釋“聞”之古字“”為“昏”,又有據諫簋不好的拓本釋“某”下“不”字為“否”者。楊先生雖沿襲誤釋,卻能據文義將此二字正確讀出,卓識可佩。白军鹏先生也主張讀“某不”為“無不”,舉證與上引楊文同。他們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盉銘下文並無用作否定詞之“母”,所以楊文“變文以避複”,之說不能成立。先秦漢語虛詞,往往因語氣的輕重緩急而發生分化。否定詞如“不”與“弗,“毋”與“勿”,原來可能都由一語分化。訓“無”之“蔑”、“末”,也可視為由“無”分化而成。“某”與“無”的關係,可能與它們相類。只不過“某”之語氣似較“蔑”、“末”為輕,而且東周以後似已不見使用。如確實如此“某”就不必改讀為“無”了[11]。 ,見於五年琱生簋“虎曰:余既訊,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亂,”,六年琱生簋“有司曰:令,”。命,在這些句子中都是遵命的意思。 稱公命,盉銘“爯”字下加“攴”旁,白軍鵬先生以為“即爯’之繁構”[12]。黃錦前先生指出,楚文字“爯”字下從“又”與此相似[13]。各家多讀“爯”為“稱”。李學勤先生引《漢書?景帝紀》:注“副也”,以為“稱”字在此是“合”的意思[14]。一葦先生說“爯即稱字,有隨、從、服、順等義。”《故訓匯纂》,第頁[15]。文若水先生認為“稱公命”,“可以理解為符合遵從公命之意”[16]。裘錫圭先生指出《故訓匯纂》:“稱”字條第66項引《漢書》顏師古注訓“稱”為“副”,所列之例如,《高帝紀下》:“稱吾意”、《孝成許皇后傳》:“稱順婦道”、《王莽傳中》:“奉稱明詔”,“稱”字用法都與“稱公命”之“稱”相同第85項引《禮記?檀弓上》孔疏,謂“稱,猶隨也”第86項引慧琳《一切經音義》,訓“稱”為“順”。用來訓“稱”的“副”當符合講,隨從、順從等義是由符合義引伸出來的[17]。 余唯自舞(無),鞭五百,罰五百寽。裘錫圭先生認為,自,即“擅自”,“自行其是”之“自”,猶“今言‘另自’,‘別自’。盉銘文是“余自無則鞭身,笰傳出。”盤銘文此處可能省略了“則”,則,法則。《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箋以“順天之法”釋“順帝之則”。無則,目無法紀,在這裡也可理解為不順公之則,即“不稱公命”[18]。在這裡是假設自己如果有這種行為,會怎麼樣。 李紀言先生把“無”讀作幠,訓作傲慢[19]。何有祖先生认为“余唯自無”下緊接著“鞭五百,罰五百寽”這樣的刑罰措施,故而懷疑“無”可能與違背“氣”之前在氣盉銘文中所發誓言有關,疑讀作“侮”。“無”字古音在明紐魚部,“侮”字在明紐侯部,聲紐相同,韵部相近,音近可通。古文字從母之字與從每之字可通作,如《孔子見季桓子》“民氓不可”,其中“”,陳劍先生讀作侮。無、毋可通作,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無逆政命”,《史記·宋微子世家》“無”作“毋”。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賦斂毋(無)度”,“毋”通作“無”。至于《昭王毀室》簡3“(僕)之母(毋)辱君王”,是母、毋通作之例。可見,“無”、“侮”有通作的可能。侮,指輕慢。《玉篇·人部》:“侮,侮慢也。”《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僞孔傳:“有扈與夏同姓,持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管子·法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文獻有“自侮”之說,如《孟子·離婁上》:“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書·甘誓》“威侮五行”之“侮”的對象是“五行”、《管子·法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之“侮”的對象是“禁”。气盉“余唯自無(侮)”之“侮”的對象當是气的誓言。自己輕慢其誓言,所以受刑罰[20]。我们同意裘锡圭先生的看法。 這句話的大意是,氣發誓說,我一定要遵從穆公的命令,給霸姬提供僕馭、臣妾。如果我違背了你的命令,就鞭打我五百下,罰我銅五百寽。 4.報厥誓曰:余稱公命,用霸姬。襄余亦改朕辭,則鞭五百,罰五百寽。 報厥誓,裘錫圭先生認為,報,在此似可理解為回報、報應[21]。董珊先生认为,報厥誓,是对上面誓言的回应,等于“从辞从誓”,即再重复说一遍上述之誓詞[22]。裘先生說對“厥誓”的具體理解他與董先生不同。他認為“厥誓”即指乞所發的“余某弗稱公命”的誓言。 在這句話的意思是氣重复说一遍上述之誓詞,我一定要遵從穆公的命令,給霸姬提供僕馭、臣妾。如果我改變了我的誓詞。就鞭打我五百下,罰我銅五百寽。 5.氣則誓:曾厥誓曰:女某弗稱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則鞭身,傳出。 曾,吴雪飞先生认为,曾訓為重。《楚辭招魂》:曾臺累榭。注:重也。《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注:猶重也。曾厥誓,即重複其誓言。曾也可能讀為增,指增加、加重其誓言[23]。我们认为,曾,训为以前。 傳出,下一句写“出弃”,都是省略,散氏盘写“传出弃”,才是完整的。传,李学勤先生,白军鹏先生,黄锦前先生皆以为指传车。出,黄文认为是“驱逐”的意思,引《左传》文公十八年“宋公……遂出。武、穆之族”,以及《晏子春秋?谏上十四》:“楚巫不可出,此为晏子对齐景公“请逐楚巫而拘裔款”之语的回答”。傳出,意思是用传车放逐违誓之人,是为了尽快将他逐出[24]。 董珊先生认为,传读“转”,运也。“出弃”见于以下文献: 《史记·范雎列传》:守者乃请出弃箦中死人。 《史记·晋世家》: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 董先生认为,傳出,出弃,传出弃,意思相近,都是把尸体转运出去,丢弃[25]。 這句話的意思是氣就發誓說,以前我發誓說:我一定要遵從穆公的命令,給霸姬提供僕馭、臣妾。如果違背了,就鞭打我,让我死去把我的尸体转运出去,丢弃。 6.報厥誓曰:余既曰稱公命,襄余改朕辭,則出棄。 曩,白军鹏先生读为当“过去、以前”讲的“曩”,裘锡圭先生同意这个看法[26]。李学勤和董珊先生认为,曩,读为假设连词“傥”,相当于古书誓词表假设之词常用的“所”。如《书·牧誓》:“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27]。 辞,白军鹏先生认为“辞”字金文中习见,亦见于匜:“汝亦既从辞从誓”,“牧牛辞誓成”气盉铭中亦有“辞”有“誓”,过去有人认为匜中的“辞”指“诉讼”,“誓”指“誓言”,现在就本铭看来是不对的,因为这篇铭文中并没有涉及到诉讼之事,所以“辞”与“誓”显然是意思近似的两个词,因此本铭言“改辞”应该就是“改誓”之意[28]。 裘锡圭先生认为从本器铭文看,“誓”与“辞”似有区别,至少对文有别。从“报厥誓”之语看,“厥誓”就应指乞所发的“余某弗称公命”的誓言。从此句的“改朕辞‘出弃’看,发誓时所说的、关于如果违誓应受何种处罚的话,虽然可以看作誓的一部分,但也可以另称为“辞”。一般认为古汉语中的“辞”可作“讼辞”讲,其实凡言罪状之辞皆可称“辞”。因此将全部誓言中的这一部分特称为“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9]。 董珊先生认为,誓言的每个部分,各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约定,正面的称“辞”,反面的称“誓”[30]。 這句話的意思是氣重复说一遍上述之誓詞說,我已經發誓說,我要遵從穆公的命令,如果我改變了我的誓言,就我死去把我的尸体转运出去,丢弃。 7.氣則誓。 氣作了發誓。 8.對公命,用乍(作)寶盤盉,孫孫子子其萬年寶用。 霸姬為了報答穆公的命令,作了這件青銅盤,希望子孫可以長久的使用它,所以這件盤,是霸姬作的,應該稱呼為霸姬盤。 由盤銘看,我們知道了氣盉銘文銘文中的公,就是穆公,這篇銘文反映了西周中期的法律,訴訟,發誓的情況以及程式,和匜銘文非常相似,大家可以參看,由於銘文古奧,我們只是做了初步的考釋和銘文大意疏通。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翼城縣文物旅遊局,山西大學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號墓發掘》,《考古學報》年第2期。 [2]吳雪飛:《周代訴訟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年,第19-23頁。 [3]“穆公”信息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 [4]帝企鵝發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qiea.com/dqefbfw/8035.html
- 上一篇文章: 抽奖三季度大量好游戏来袭搓手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