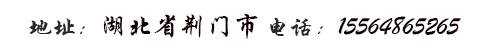二时代董晓可一盏温暖的守望之灯张红兵
|
一盏温暖的守望之灯董晓可 二时代 读诗:我一直徘徊在你的身影里(伊丽莎白·白朗宁) 一盏温暖的守望之灯 ——张红兵诗集《十年灯》简评 在中国藏民族,流传着这样的风俗,夜行走山路的人们很忌讳别人拍肩膀。他们认为,双肩之上有神灯守护,倘若被拍灭,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在古希腊神话中,哈里希岛上有一盏长明灯,那是姐姐为远航的弟弟点亮的。遗憾的是,孤寂的灯塔最终未能挽回弟弟,但却挽救了许多捕鱼归来的船只。可见,灯,在无论哪个民族,都是温柔和光明的存在。而守望一盏灯,于漫漫长夜之中,大抵也该是温暖的事情吧。在这个列车提速、飞机提速、甚至爱情和婚姻都在迅猛提速的时代,张红兵却用十年光阴,以拙朴的笔体默默耕耘在诗歌的国度里。十年一部诗集,足见他对诗歌事业的珍视。而他那盏诗歌王国的小灯,也凝结了自己绵密的情感,闪烁着独有的精神烛照。 1 作家聂尔在《十作家书》中有过这样的论断:“极端地说,现代作家所写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互文,甚至直接都是引文。”诚然,经典压制是当下每一位清醒的作家(包括诗人)都足该警惕的,而保持独立和超越的清醒认识在创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绘画艺术的高校教师,张红兵在诗歌意象的构筑上,并未像诸多平庸诗人那样因循着《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典范式,邯郸学步地简单写景抒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他是真正能对这个时代“读心”的人。在对诗歌艺术的阐释上,他借用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杜米埃的色调,借用了他厚重的色块和线条,借用了他深沉的悲悯情怀。他在《杜米埃怎么会是脏的、暗的》一诗中这样写道: 杜米埃怎么会是脏的、暗的/只是他的绘画有些脏有些暗罢了 杜米埃的绘画怎么会是脏的、暗的/只是他混迹其中的三等车厢有些脏有些 暗罢了 杜米埃混迹其中的三等车厢怎么可能是脏的、暗的/只是坐在他对面的旅客有些脏有些暗罢了 可是,旅客怎么会是脏的、暗的/最后只能将问题归结到杜米埃身上 是他的身体里积压了太多又脏又暗的颜料/他必须一点一点将它们转移到画布上 在此,笔者借用这首诗,是想说明对张红兵诗风的整体感受。在他的作品中,很难寻觅到那种俗世的乐观,而更多的是一种对寒风般呼啸而过的流光下芸芸众生的痛楚、无助的悲悯和爱意。去年深秋时节,在阳城采风期间,张红兵同笔者交流了对当下商业大潮中人的生存境遇的隐忧:人们昼夜不停地穿梭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中,超负荷地劳心劳力。孩子从两三岁即被送入幼儿园,融入了长达20年左右的千人一面的流水线式的学习生涯;尔后是步入社会艰难的工作、结婚、房贷、抚养孩子的历程。乡村被掏空了,人们再也回不去那方诗意的故园……所以,他只能为尘世中卑微的个体感慨,一如他笔下的《石榴花》那样:“是花,总得开在六月酷烈的阳光下/石榴花不像是在开/倒像一个找不到家门的孩子/在黑夜中不停地哭喊/他就那么一朵一朵地/哭喊出它内心的恐惧和孤独”。是啊,有多少人在这个社会中彷徨,在人生的轨迹中迷失了方向。 作为一个诗人,张红兵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他只能像画家杜米埃那样,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的颜料”一点点地挤出来。但他的诗歌却并未因为这些感受而染上晦暗、阴冷的色调,事实上,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更多的是触碰到一种柔性的温情,一种低调的温婉,一种氤氲在心灵深处的感动。在这个漂泊不定的现实世界,他是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灵动的个体,活出自己的本真来,就像那些秋虫一样“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不管是初秋,还是季末/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他们用短暂生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再次写到秋虫》)。那种秋虫的叫声,大抵就是庄子所说的天籁之声吧,大抵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我们所能感知并真心向往的最好听的声音吧。 2 来说一说他的情感吧。 “暖”和“真”,是张红兵诗情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特色。 先来说说他的诗歌之暖。 读他的诗,我们常常能被一种充满爱意的温情所感染。正如诗集标题《十年灯》所言,他用自己的诗歌于暗夜中点亮一盏灯,给人带来了丝丝暖意。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沉浸喧嚣久违天然的情感,如同一页褶皱的纸片在心灵感召下的复苏:“从寒冷开始,从虫子开始,从牛羊的馋嘴巴开始/从不停地挣扎和抵抗开始,从试着爱上风雨和炎热开始/还得从汗水开始,从小心的锄头开始,从弯着的腰开始/最后,才是请求饱满、金黄,才请求那一点点干净、温暖的光辉”(《干净、温暖的光辉》);在他的笔下,人和自然生灵是心灵相通的,是温馨共存的,比如那些乖巧的萤火虫:“萤火虫是属于乡村的/萤火虫是牛粪变的/像母亲的另一群孩子/她要捉一个或几个来/取悦她从城里回来的孙子/萤火虫真是乖孩子/多么善解母亲的心意/直往母亲的怀里扑/他们更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萤火虫》);在他的笔下,亲人间的感情总是那么真挚,那么富有传递性,比如那把桐木短剑:“一年了,儿子依旧不时挥舞在手中/一年了,父亲恐怕已经忘记/一年了,木香早已散尽/一年了,剑上尚有父亲手的余温/一年了,我也是偶尔握一握/就像触到了父亲的手”(《桐木短剑》);在他的笔下,心灵的柔弱在爱人的怀抱中可以毫不羞涩地展露,一如返航的小帆在避风的港湾里安稳寄宿休憩:“手术后身体的痛苦和虚弱/还不足以让我失掉系鞋带的能力/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莫名地产生了依赖//你蹲下弯腰的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就像个孩子”(《我就像个孩子——给妻子》)。对于“幸福”,有人做过这样的诠释: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如果这个解读成立的话,那么张红兵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张红兵的诗歌也应该是幸福的诗歌。因为他是能真切感知这个世界温暖色调的人,因为他的诗是能让人有温暖如春感受的。 再说说他诗歌之真。 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张红兵诗歌的情感是极其真挚的、赤诚的,这是其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他的诗中你几乎看不到那种打太极似的花架子,他总是以最精粹的瞬间意象,最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心灵世界。 年初冬,他去湖南参加全国“青春诗会”,在岳阳的南湖宾馆院子里,碰到了一个中年女子。这个女子只有一条腿,拄着拐,但她肩上挑着担子,箩筐里是刚刚从山上采回来的野蘑菇。数年过去,这个情景仿佛一个结,一直深深地嵌在诗人的脑海中无法解开,后来一首名为《多余之诗》的作品诞生了: 至今,我仍觉得我的双肩是多余的 我肩上没有担子,没有担子两头的箩筐 箩筐里的野蘑菇,蘑菇身上的露水 至今,我仍觉得我的两条腿是多余的 比一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接下来 我用两条腿走出来的步履也是多余的 一根拐杖帮一条腿走出来的 留下一双双不对称的“脚印” 甚至,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多余的 因为,她是一个只有一条腿仍在走路的女人 我甚至觉得,多年来,我郑重其事的诗歌 也是多余的,无论它曾经以怎样美好的名义 在此,我们能看到诗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面对这样一个失腿拄拐、背负箩筐的弱势个体,诗人的情感波澜是极其强烈的。在诗歌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诗人对生存意义的思索、对诗歌意义的思索,是带着一种复杂的甚至有些悲愤的情感的。在这个女子面前,诗人看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看到了在这样让人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现实面前,一切生存抑或诗歌“意义”诠释的轻浮,因为与之形成对照的还有生存、挣扎、活着等沉重主题。在一句句“双肩”、“双腿”、“作为男人”、“诗歌”等的多余中,好似一锤锤重鼓,不断敲击着读者情感的鼓面。 什么是情感之真?古人将其总结为赤子之心。前不久获得首届孙犁散文奖的作家汗漫也认为,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有一个怎么真诚面对世界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道德和伦理。是的,真诚,在这个日渐喧嚣和浮躁的尘世,不虚浮、不造作、真诚地审视和表达心灵感受,变得多么可贵。在张红兵的诗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真情流露,这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也是一种略带痛苦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在情感的天平上,张红兵是不惜力的,读他的诗,总有一种力透纸背的感觉,这种“力”中,真诚情感的因子占据很大份额,这也正是他诗歌常常能触动人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真挚情感,在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涓涓细流的诗意之外,还展现了一种“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刚烈猛劲的诗风。如在《看襄垣秧歌剧豫让与襄子》中,诗人这样写道:“自鲁迅以下我已不敢轻言精神的胜利/我怕将我和阿Q归为同类/但我尚能看见我的心,看见我的为人/当豫让最后将匕首击向襄子献出的锦袍/我的眼中刹那间涌满了泪水”。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诗人借助对“豫让刺赵襄子”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的激昂抒发,迸发着其内心涌动的源自灵魂深度的对人类高贵精神深深服膺和强烈震撼的炽热感情。而正是这种跃动的、真挚的感情,也强力触动着读者的心。 3 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镌刻着这样一个神谕——“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激励着一代代学人勇敢地正视自己的人生。同样地,作为一个有自省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张红兵诗歌的很多地方,都不动声色地潜藏着对自我的理性审视,而这种审视集中地呈现在他作为诗人的身份上。在他看来,诗歌事业是神圣的、可以烛照灵魂的,这也正是《十年灯》名称的寓意,而与之相对的诗人在沉重现实中之处境却常常让人唏嘘哀叹。在《耻辱书》中,诗人这样写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圣贤的语录像一面镜子/让我看清了自己/我愧对这样的太平盛世,内心满怀羞耻/高堂父母,皆已年逾古稀/他们仍然在风雨中劳作/仍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每当想到这些/我的耻辱感就又增加了一重”。这种对贫贱的耻感和对自我的嘲讽,隐含着诗人发自内心的痛楚和无奈。 在《雪》一诗中,他又借助阿多尼斯,这位因写诗批评自己的祖国而被迫流落他乡的黎巴嫩诗人,来抒发对诗歌于现世之力量微茫以及诗人无所皈依的漂泊境况的感慨:“我暂时离开配图里的阿多尼斯/仿佛不忍心看他一头的白发/他坐在书房里如坐在雪地中/他写了那么多诗歌/但一切都不曾改变/一场雪就轻易改变了这个世界/多少年,我也一直站在雪地里/我的头发也已变白”。是啊,数十年跋涉诗路,直至皓首而立,这样的执着究竟在追求什么,诗人的这种自我追问事实上也在叩问着世道人心,叩问着现世中对诗歌坚守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精神、意志和信仰,是不会被残酷的、微凉的尘世吞噬掉的。而作为一个诗人,本就应该像阿多尼斯那样,有自己磐石一般的坚守,有自己为之诗者的高贵的不与世庸俗之气共谋的神圣节操,这正如他发自内心对象征当下流俗的“亲”字的坚决否定:“在这个“亲”字你追我赶的时代/就让我做一个落伍者/就让我做一个殊死抵抗的人/做一个说出一万个“亲爱的”都不嫌多的人//亲爱的,我们沆瀣一气/仿佛那样不合时宜地努力/就是为了赢得强大世界赐予我们的羞辱”(《亲爱的,而不是“亲”》)。 在诗集的后记中,诗人写道了帝企鹅的生存故事:帝企鹅每年要长途跋涉一个月,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去恋爱、产蛋。小企鹅出生后,母企鹅又要花费两个月时间往返海边去觅食,然后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给他们带回食物。在这期间,小企鹅难免会被冻死或者饿死,母企鹅在途中有的也会遭遇不测。这种生存方式,让企鹅族群的存活率产生了自然的降低。 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什么力量操纵着它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不断地去追求一种安稳生活以外的、冒着生命危险的存在方式?这大概只能解释为生存的法则吧。而诗人之宿命,是否在冥冥之中,也早已如帝企鹅一样,被缪斯女神一一安排。“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或许古人早有指引,他说,你来,点亮这盏长夜孤灯,烛照自我,也烛照世界,美好地期待着它一直亮下去。 原载《太行文学》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董晓可,现居山西高平,作品散见于《西南作家》、《黄河》、《太行文学》等刊,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在读。 往期精彩二时代 灯光微弱,照见一个人(戈多) 铃兰花开:我就在你身后,离你很近的地方(组诗) 二时代 我们坐下来聊聊好吗? 二时代 阎连科:猜测川端康成之死 二时代 焦丽萍:青瓷盘 二时代 董春花:我和女儿 阅读 往期 点左下角“阅读原文”查阅往期作品 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iqiea.com/dqeqxhj/1399.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早餐直击东北经济吉林行
- 下一篇文章: 刚刚刘强东宣布当村长,马云狂撒100亿